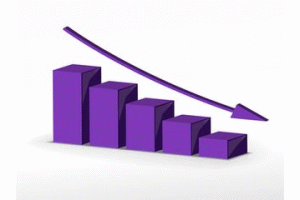深度|“降電價”背后的邏輯
“臨時性降價”成為各地首選
4月9日上午,國家發改委在京舉行“清理規范經營服務性收費、減輕企業負擔取得實效”專題新聞發布會。會上,張滿英介紹了“一個目標、兩個方向、八項措施、兩批實施”的降電價工作總體部署。即:一個目標,這次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10%,要不折不扣地落實到位;兩個方向,降低電網輸配電價水平,以及清理和規范電網環節的收費;八項措施,清理和規范電網環節收費,釋放區域電網、省級電網和跨省跨區專線輸電工程輸配電價改革紅利,降低電價中征收的政府基金標準,釋放減稅紅利等八項措施;分兩批實施,一批措施已經發文,即發改價格〔2018〕500號文,涉及金額430億元,從4月1日開始執行;第二批計劃下半年實施,正在抓緊研究論證中,涉及金額400億元。
發改價格〔2018〕500號文發布后,各地紛紛行動,出臺了各自的降電價措施。其中,北京市4月1日起對本市郊區(含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一般工商業用戶的電度電價每千瓦時下調1.53分;2017-2019年北京電網輸配電價中一般工商業及其他用戶的電度電價每千瓦時下調0.51分。江蘇省宣布一般工商業及其它用電類別電價每千瓦時降低2.29分。4月23日,湖北省物價局發布調價通知,一般工商業及其他用電電價每千瓦時降低0.02564元,電價調整政策從2018年4月1日起執行(含當天抄見表量)。
從各地已出臺的“降電價”措施看, “臨時性降價”成為首選,這不失是簡便直接、立竿見影的手段。當然,我們不能把政府管理電價都歸結為計劃經濟手段。電力作為特殊商品,只要存在壟斷或者市場失靈,價格管理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同樣存在政府直接制定或者干預價格的情況。更何況我國距建立成熟的競爭性市場、由市場決定價格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這種“臨時性降價”并不能完全解決我國工商業電價高的問題。
解鈴還需系鈴人,我們需要找準導致工商業電價高的原因所在并對癥下藥,才能防止工商業電價階段性降低后再反彈,并以此為契機進一步理順電價形成機制。
工商業電價高是定價機制不順的典型體現
一個國家電價的高低很大因素是由資源稟賦來決定的。我國一次能源稟賦并不是太好,美國到場煤價5000大卡長期穩定在40美元/噸左右也(300元/噸左右),而我國煤價是長期高于這個價格,2017年因去產能達到了近700元/噸。
根據國際能源署2016年8月發布統計資料和部分亞洲國家電價資料,2015年,我國居民電價在31個國家中居于倒數第3位,僅高于墨西哥和馬來西亞;但是工業電價居于第16位,大體處于中間的位置。我國電價總體處于國際中等偏下水平,平均電價與美國接近,但是工業電價至少高出美國50%。
電價要反映電壓等級和負荷特性,負荷特性反映用戶的用電行為和對系統設備的使用效率。居民用戶負荷率低、供電電壓最低,輸送距離最長,因而其供電成本在各類用戶中最高,從而電價水平應最高。而工商業用戶負荷率高和供電電壓等級高,輸送距離短,供電成本低于系統平均水平,從而其電價水平理應較低。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工商業電價均大幅低于居民電價。例如,2015年美國的居民電價約為商業電價的1.2倍和工業電價的1.9倍;OECD國家的居民電價約為商業電價的1.1倍和工業電價的1.5倍。而我國居民電價卻長期低于工業電價,據張滿英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目前全國平均銷售電價的水平是每千瓦時0.65元,其中居民電價0.55元,農業電價0.48元,大工業電價0.64元,一般工商業電價0.80元。
我國工商業電價由上網電價(燃煤標桿電價)、輸配電價、輸配電損耗和政府性基金四部分構成,主要有五方面因素導致了這種電價信號的扭曲。
其一,容量電費和分時電價在執行中反而大幅增加了工商業電價成本。設置容量電費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發電和電網資產的利用效率,促進企業合理用電。但是,大部分企業申請用電時習慣性按最大用電負荷配置變壓器容量,當企業實際生產需求與變壓器配置容量不匹配時,負荷率水平較低直接造成容量電費過高,最終體現在企業單位用電成本高。除了容量電費外,分時電價政策是導致工商業電價成本高的另一個原因。當前的分時電價政策基本是一刀切,絕大多數企業不僅不能利用分時電價政策降低用電成本,反而拉高了用電成本,反而是一些高能耗如水泥企業在避峰生產,降低了用電成本。
其二,交叉補貼直接推高了工商業電價。政府出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保證民生等方面考慮,對部分種類用戶實行優惠電價,如居民、農業、重要公用事業和公益性服務等。在電網企業電費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優惠電價部分由一般工商業電價和大工業電價彌補。這種存在電價類別之間的交叉補貼帶有典型的區域性,越是老少邊窮地區和工商業落后地區,其工商業電價負擔的交叉補貼就越重。這種交叉補貼不僅僅存在于電價類別之間,還存在于地區之間,如廣東省的粵西、粵北地區與珠三角地區經濟實力差距巨大,同類型電力用戶,在廣東不同地區用電價格是不一樣的。
其三,基金附加和稅金加重了工商業電價負擔。基于國家重大戰略工程建設需要,我國電力長期以來承擔了商品之外的許多功能。目前,電價附加中有四種在全國范圍內征收的政府性基金——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0.7分)、水庫移民后期扶持資金(0.83分)、農網還貸基金(2分)和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1.5分),總計5.03分。各地還有地方性的基金,如四川省電價里有一項0.05 分的小型水庫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其四,電力運行效率性因素增加了工商業電價成本。工商業電價中有一部分是輸配電價和輸配電損耗。雖然,我國在2017年完成了對32個省級電網輸配電價核定工作,核定并公布了華北、華東、華中、東北、西北區域電網輸電價格,跨省跨區輸電價格也正在核定之中。獨立的輸配電價從無到有,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但由于缺乏專用的管制會計準則,現有的輸配電價并沒有厘清電力運行的真實成本,電力運行的低效往往以成本方式轉移到工商業電價上。例如,有的輸電通道常年實際運行負荷不到設計容量的一半,“三棄”問題仍持續困擾電力發展,這類系統運行中的低效甚至負效最終還得由電力用戶來買單。
其五,電價雙軌制使得工商業電價喪失市場紅利。2015年3月,中發9號文啟動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以來,我國電力市場化交易機制初步建成,市場化交易電量快速增長,2017年國家電網公司區域市場化交易電量達到12095億千瓦時,占總售電量的31.2%,通過電力直接交易降低客戶用電成本295億元,平均降低電價3.3分/千瓦時;南方電網經營區域內,四省區市場化交易電量2680億千瓦時,占總售電量的30.1%,累計為用戶側減少電費支出217億元,平均降價8.5分/千瓦時。各省市電力市場化程度不一,一般工商業用戶參與電力市場化交易也程度不一。即使是電力市場化開放程度最高的青海,最先獲得市場紅利的也是大工業用戶。在電力市場化開放程度較低的京津唐、上海、浙江等省市,一般工商業用戶仍然完全被排除在電力市場化交易之外。
作者:劉亮 來源:中國電力企業管理 責任編輯:jian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