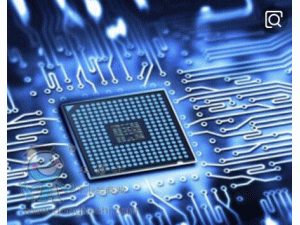比“兩彈一星”更難?一文讀懂中國半導體發展8大困境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半導體已經長成為一個巨人,1美元半導體產品可以撬動100美元GDP。
上個月,美國兩黨參議院先后提出《為半導體生產建立有效激勵措施》《美國晶圓代工業法案》,呼吁投入370億美元以維護本土半導體戰略競爭優勢。
資本和研發投入對保持半導體行業的競爭力至關重要。而中國要想爬上這個巨人的肩膀,眼前要邁過的坎不只是錢和研發這么簡單。
中科院半導體研究所研究員、半導體超晶格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駱軍委和中科院院士李樹深曾花了10個月的時間進行調研,摸清了中國半導體科技發展的真實現狀,以詳實的數據和資料闡述了當下國內半導體科技面臨的八大困境。
困境1:歷史積累厚、技術更新快
2015年,作為全球手機芯片霸主的高通宣布進軍服務器芯片市場,并正式對外展示了其首款服務器芯片,不到3年就遭遇重重挫折而退出;從2010年到2019年,英特爾在移動芯片努力了十年,但始終未能撼動高通的地位,最終先后放棄了移動處理器和手機基帶芯片兩大業務,告別了移動市場。
這兩個例子告訴我們,即使是財大氣粗的高通和英特爾,想要在半導體領域拓展新的市場,都是九死一生。半導體并不是有錢就能干的。
半導體產品的特點是性能為王、市場占有率為王。它一方面需要長期的歷史積累,另一方面還要應對技術的快速更迭。
常有人把半導體研究與兩彈一星作比較,認為中國人能做出兩彈一星這樣的尖端科技,半導體也理應如此。但人們忽視了,兩彈一星技術一旦掌握,自我更新速度較慢。半導體是按照摩爾定律高速發展的,單位芯片晶體管數量每18個月增長一倍。
在半導體領域,落后一年都不行。一步慢,步步慢!
困境2:研發成本大、進入門檻極高
國際半導體大公司的平均研發投入長期保持在營業額的20%。2016年,研發支出大于10億美元的全球半導體公司有13家,前十名的投入總計353.95億美元,其中英特爾高達127億美元,2019年增長為314億美元。

困境3: 產業鏈條長,擁有最尖端的制造水平
在過去半個世紀里,以8個諾貝爾物理學獎12項發明為代表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半導體科技。要支撐半導體技術頂層應用,從材料、結構、器件到電路、架構、算法、軟件,缺一不可。
從沙子到芯片,總共有6000多道工序,前5000道工序是從沙子到硅晶片。目前,中國12英寸硅晶片基本依賴進口,無法自主生產。
有了硅晶片之后,集成電路產線中的芯片制造又有300多道工序,其中100道與光刻機相關。光刻工藝是半導體制程中的核心工藝,也是尖端制造水平的代表。一套最先進的阿斯麥nxe3350B EUV光刻機售價為1.2億美元,并且是非賣品。
另外,半導體芯片制造涉及19種必須的材料,大多數材料具有極高的技術壁壘。日本在半導體材料領域長期保持著絕對的優勢,硅晶圓、化合物半導體晶圓、光罩、光刻膠、靶材料等14種重要材料占了全球50%以上的份額。像光刻膠這樣的材料,有效期僅為三個月,中國企業想囤貨都不行。
中國的化學很強,化工卻很弱。目前,國內芯片制造領域所有的化學材料、化工產品幾乎全部依賴進口。
困境4:受到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技術限制
1美元半導體產品可以撬動100美元GDP,任何國家都想牢牢抓住這一產業。根據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的預測,增加1美元半導體科研經費,可以使GDP提高16.5美元,這樣的投入很“劃算”。
1986年,日本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半導體生產國,美國為了打壓日本,一方面出臺各種政策鼓勵其國內企業研發制造,另一方面在1986年簽訂了《美日半導體協議》,限制日本半導體對美國的出口,同時要求日本必須進口20%的半導體產品,從而在1992年重新奪回世界第一大半導體生產國的地位。
如今,美國面對競爭者同樣是步步緊逼。
2017年,白宮出臺《確保美國在半導體行業長期領先地位》的報告,包括美國總統科技和政策辦公室主任以及各大半導體企業、投資機構、咨詢公司CEO和科研機構頂級專家組成的工作組,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和措施。
其中就包括:建立新的機制,讓企業的專家參與半導體政策和挑戰;成倍增加政府投入半導體相關領域的研究經費;實施企業稅收政策改革;實施包括通用量子計算機、全球天氣預測網、實時生化恐怖襲擊探測網等一些列“登月”挑戰計劃來促使半導體技術的創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還提到,要動用國家安全工具應對中國的企業政策;加強全球出口控制和內部投資安全(防止中國產生獨有技術)。
作者:駱軍委 來源:科學網 責任編輯:jian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