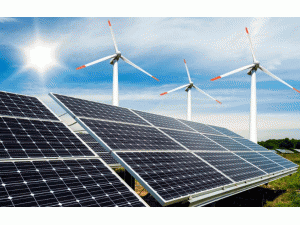構建“新”能源體制是“十四五”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關鍵
2020年9月22日,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我國將努力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在全世界引起重大反響。這不僅給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了新的壓力和動力,同時進一步明確了我國能源轉型方向是低碳和零碳能源,經濟轉型的方向是“碳中和經濟”。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當前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和能源低碳轉型面臨的體制和政
2020年9月22日,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我國將努力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在全世界引起重大反響。這不僅給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了新的壓力和動力,同時進一步明確了我國能源轉型方向是低碳和零碳能源,經濟轉型的方向是“碳中和經濟”。
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當前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和能源低碳轉型面臨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如果在“十四五”期間不能得到有效解決,“碳中和”的遠期壓力將很難有效轉化為近期動力,“十四五”我們可再生能源發展恐將進入“瓶頸期”。
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實施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對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價格、財稅、金融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可再生能源產業進入快速發展期。根據《BP世界能源統計2020》的數據,截至2019年,我國可再生能源(含水電)消費總量達到17.95艾焦(相當于4.99×1012kWh),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含水電)消費量中的占比高達26.9%。2006―2019年,我國可再生能源消費量年均增長11.5%,而同期我國化石能源消費量年均增速為3.4%。2019年,我國繼續保持世界第一大可再生能源消費國和生產國的地位,可再生能源(含水電)消費總量分別相當于美國(全球第二)的2.2倍、巴西(全球第三)的3.2倍。特別是,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為全球碳減排做出重要貢獻,2019年消費的可再生能源(含水電)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6.5億噸,占我國當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16.5%。
然而,可再生能源這一快速發展的勢頭恐難延續。盡管隨著技術不斷創新,發電成本大幅下降,成本問題不再是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主要障礙,但由于短期能源政策重點變化的不利影響,加上既有能源體制無法協調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的利益沖突,促進可再生能源良性發展的新體制構建問題也未被提上日程,可以預期,“十四五”期間,既有能源系統對可再生能源的容納能力將逐漸下降,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可能進入一個“瓶頸期”。
一、外部和內部壓力導致可再生能源的戰略地位發生變化
2020年,面對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和我國經濟的沖擊,中央提出了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基層運轉、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等“六保”經濟工作任務。能源領域的“六保”任務直接體現在2020年6月國家能源局發布的《2020年能源部門工作指導意見》中,“保障能源安全”重新被列為能源政策最優先地位。《指導意見》中的“政策取向”部分第一條明確提出“以保障能源安全為首要任務”,第二條強調要“堅持以惠民利民為根本宗旨”。盡管《指導意見》也提出了“堅持以清潔低碳為發展目標”,但可再生能源電力存在一定間歇性和波動性,現在的成本也偏高,所以,可再生能源難以完全匹配“能源安全”與“惠民利民”的要求。在“能源安全”優先、“惠民利民”次之的能源政策定位下,可再生能源的戰略地位下降是必然的。
此外,我國在巴黎氣候大會上的承諾是近年來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最直接動力。2018年,我國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累計下降45.8%,提前兩年實現2020年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國際承諾;2019年,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為15.3%,提前一年實現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的國際承諾。能源政策優先次序的調整,疊加國際承諾的實現,直接削弱了我國可再生能源在“十四五”期間的發展動力和壓力。
二、可再生能源在既有電力系統和電力體制中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有限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作為推動能源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手段,進展最快的是電力部門中風電和光伏發電量的快速增加。但是,這種變化不單純是電力系統中化石能源與可再生能源份額此消彼長的替代過程,必須伴隨著電力系統的轉型。因為風電與光伏發電具有間歇性和波動性特征。
隨著風、光發電比重的上升,必然要求電力系統以更高的靈活性來應對這種波動性。根據歐洲國家能源轉型的經驗,能夠提升現有電力系統靈活性且邊際成本相對低的技術手段有如下幾種:一是對燃煤機組和熱電聯產機組進行靈活性改造;二是利用技術、經濟等方面的綜合手段提高電力需求側靈活性;三是優化相鄰電網互聯互通,提高相鄰電網的“間接儲能”功能;四是在風電場和光伏電站增加儲熱裝置;五是采用儲能技術提高電力系統靈活性。同時,電力系統還需要適應用戶側“產銷者”的增加,以及新的商業模式出現,利用數字化技術提高配、售、用電環節交互能力和響應速度,推動電力系統向分布式、扁平化轉變。
目前,我國提高電力系統靈活性的主要舉措是煤電機組的靈活性改造。其余4種途徑則由于體制和利益障礙,或進展緩慢,或效果有限。然而,更重要的是,上述5種提高電力系統靈活性的技術措施,需要制度上的靈活性保障:歐洲不僅一直在完善統一的電力市場制度,而且充分考慮到針對風、光發電的波動性影響來修正原有的電力市場交易和監管制度。電力系統技術上的靈活性決定了靈活性資源的數量,是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的基礎,而市場制度靈活性決定靈活性資源的配置效率。盡管我國電力體制改革在穩步推進,但有利于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一些改革舉措,比如輸配電價改革、可再生能源直接交易、增量配網改革等進展和成效有限。此外,提高電力系統靈活性的方法主要側重于個別技術路徑。“十四五”期間,除非我國能夠按照能源轉型的要求,通過深化改革大幅提升電力系統的靈活性,否則在既有的電力系統和電力體制中可再生能源進一步大規模發展空間有限,可再生能源從高速增長轉向低速增長成為必然。因此,電力體制改革進程和效果滯后于能源轉型需要是“十四五”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進入“瓶頸期”的主要原因。
三、可再生能源利用技術進步在“十四五”期間難以突破既有體制的制約
能源轉型的政策架構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來建立和完善:一是以電價、稅收優惠和補貼為主要手段的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二是對既有體制和政策中妨礙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部分進行改革和修訂。這兩類政策和體制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激勵可再生能源技術和低碳技術開發,降低技術成本,培育可再生能源的市場競爭力,最終離開補貼等政策的扶持。自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實施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對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價格、財稅、金融等一系列支持政策。
其中,風電和光伏發電的補貼政策持續時間最長,盡管一直存在補貼拖欠問題,但這一政策對風電和光伏發電的技術進步―規模擴大―成本下降的良性循環起到積極作用。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數據,2010―2019年,我國陸上風電項目的平均平準化度電成本(LCOE)從0.482元/千瓦時降至0.315元/千瓦時,10年來下降了35%;海上風電項目的平均LCOE從1.186元/千瓦時降至2019年約0.75元/千瓦時,10年來下降了37%。光伏發電(非居民屋頂)的平均LCOE從1.16元/千瓦時下降到0.44元/千瓦時,下降幅度為62%。
就成本而言,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風電和光伏發電均已具備用戶側平價上網條件。2020年年底,我國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補貼政策即將停止執行,海上風電項目補貼政策從2022年起停止執行。在基本解決成本問題的情況下,電力系統靈活性就成為影響風電和光伏發電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因素。并且,目前的電力體制改革對能源轉型的這一要求似乎回應也不夠。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地方通過鼓勵光伏發電站配套儲能的方式來推動產業發展。
盡管“十四五”期間光伏發電成本仍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但考慮到持續降電價的改革政策取向,光伏+儲能的發展空間也不會太大。就是說,技術進步導致的成本下降在“十四五”期間很難突破既有電力系統和體制的約束。至于“十四五”之后,風電、光伏發電成本再次出現大幅下降到分布式發電獲得極大競爭力的那一天,或是電網資產逐漸走向貶值的拐點。這或許是我國能源轉型不得不付出的制度成本。
總之,我國由于能源轉型與能源體制改革的疊加,體制改革的進程和效果難以滿足能源轉型和創新的需要。隨著可再生能源規模擴大導致的技術、利益、體制問題交織在一起,我國的能源轉型之路必然比歐洲國家更加曲折。我們只有對可再生能源因體制約束或改革滯后而步入發展“瓶頸期”足夠重視,并在“十四五”期間通過深化改革和創建新機制等方式,構建一個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真正有利于能源轉型的“新”能源體制,可再生能源發展才能真正步入“康莊大道”。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所能源經濟室主任)
作者:朱彤 來源:《風能》 責任編輯:jianping
太陽能發電網|www.www-944427.com 版權所有